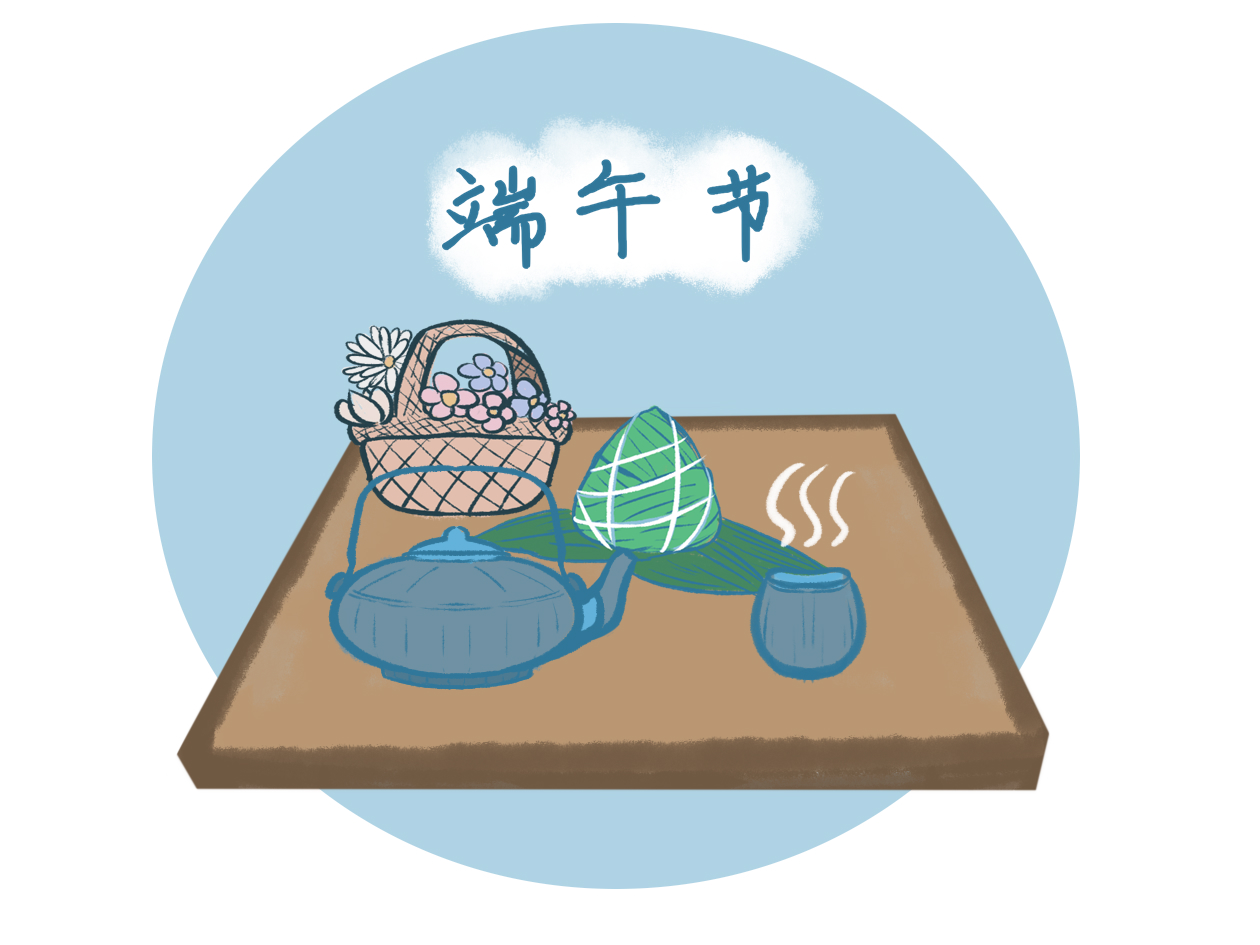图片/网络
宋辞说:渺渺,山风不歇,海水不涸,我绝不负你。
卿渺渺说:山风既歇,海水若涸,我依旧不负你。
后来,他君临天下,她母仪天下,他当着朝臣的面说,卿渺渺这辈子都是朕的皇后,君无戏言。
只是,帝后和鸣,越来越远,越来,越远……
1.
卿渺渺趴在回廊上,看着满天星空裹着的锦熹宫,清寂得让人怀疑,从前她与宋辞那般深夜不歇的恩爱,是一场梦。
如心拿着团扇给卿渺渺扇着,轻声喃喃着,“娘娘,天气热,奴婢替你拿冰粒浸了果子,你吃上几个吧。”
“不了,他再也不会来锦熹宫了,用不着这么讲究。”卿渺渺垂着眼眸,眼底透着一丝恨意,又带着三分悲寂的凉薄,“今日是中秋节吧,从前每年这个时候,我都会与他登上宫楼,他说过,每年都要与我一同放宫灯,放眼看着京城昌荣的,这才几年,他就食言。”
“娘娘,皇上还会想起你的好的。”如心不忍心地看着卿渺渺。
卿渺渺咯咯地笑着,笑着笑着,眼底温湿,天空上突然大放光彩,那炫亮的烟火,把半个宫殿都照亮了。
卿渺渺从夙离手上接过一杯茶,她抚捻着茶杯的纹路,上面有一处咯手的磕痕,是半年前宋辞最初一次来凤熹宫时,他摔的杯子,只是杯子恶劣,没被摔烂。
那日宋辞说,让卿渺渺回去劝他的父兄,放下兵权,放下权势,自损名声,他可以让卿家享尽一世殊荣。
卿渺渺拿捏着茶杯,恍恍失笑,“皇上,卿家的一切,都是你给的,你要拿回去,一句话的事,今日是兵权,明日是卿家的命,是不是,下一个,就该轮到臣妾这个一无用途的妇人身上了,皇上可还记得,你说过,卿渺渺这辈子都是你的皇后,你不会废后的,也对,活着是皇后,死了不就得啊么?”
宋辞恼怒地瞪着卿渺渺,“卿渺渺,你狂悖。”
卿渺渺隔着泪目,“卿家生我育我,我护着他们,怎样就狂悖了?”
宋辞夺过卿渺渺的茶杯,丢摔在地,满殿宫女跪了一地,宋辞冷笑,“皇后行为乖张,即刻起罢去六宫主权,禁于锦熹宫,无诏不得出。”
卿渺渺倔强地望着宋辞,两人四目相对,直至宋辞愤然离去,她豆点大的泪水才顺着眼角,滑落下来。
后来,锦熹宫的宫人,一个一个地离开,最初只要从卿府出来的如心,还有一个夙离留下来。
卿渺渺转目望一眼低头恭顺的夙离,她是个极少话的人,从前卿渺渺对她没有太大的印象,但她的确是个规矩的丫头。
2.
苏渺渺是相府的二姑娘,长姐卿小小嫁了一个商贾,日子过得挺和顺的。
母亲说,她给两个女儿许名小小,渺渺,就是希望她的女儿只需嫁得一个如意郎君,不沾染半分权势,一心一意便好。
母亲说,她看着父亲在野中半生沉浮,伴君如伴虎,她的儿女只需做个普通的人,平平淡淡把这辈子走完,就是最大的奢望了。
卿渺渺不断认同母亲的话。
卿渺渺第一次见宋辞,是在元宵节的花灯会上,那年她十五岁,对所有美好的东西,都是心之向往,比如,好看的灯笼,比如,系在灯笼下面,好看的玉坠,又比如,好看的男子。
卿渺渺看上灯笼上面系着的一个血红玉坠,她激动地拉着如心的手,“如心,你看,那个玉坠很好看,我们想办法把它拿到。”
如心摇头,“小姐,那些个玩意,还比不上你屋里随便一个耳坠值钱,我们喜欢,就去如意坊随意挑,就不跟大家争这玩意了。”
卿渺渺微斥,“如心,你是不是觉得,我一定猜不出来那个谜语,才这么说的,千金难买心头好,懂不懂。”
如心讪笑,“小姐,你又不像大小姐,我们本来就猜不出来,就别跟本人较劲了。”
卿渺渺不服气地拉着如心往里面挤进去,“我还不信了,我跟大姐都是同一个夫子教出来的,大姐懂的东西,我也懂。”
灯笼上面写着一个谜语:飘渺薄云舞,悠悠女鬼现。(猜一字)
卿渺渺喃喃读着谜语,想了许久,也没想出个形来,她撇着嘴,“如心,走吧,我们去如意坊买几个这玩意,能用钱处理的事情,何必用脑。”
卿渺渺刚想走,就听到旁边一个男子温磁的声音,“飘渺薄云舞,悠悠女鬼现,魂字。”
卿渺渺盯着男子看了半会,单纯的觉得他好看,她想起姐姐成亲时,描述姐夫身姿挺拔,面如玉冠,风度翩翩,大抵就是这般容貌吧。
老伯把那个灯笼取下来,递给宋辞,“公子,好彩头,要不要再猜一个?”
宋辞接过灯笼,从上面取下玉坠,温儒地笑着说,“夫子,心头好这种东西,一件就够了,再多就显得没意思了。”
宋辞侧目看着卿渺渺,“姑娘,你说对不对?”
“呃?”卿渺渺缓过神来,点头,“那是自然的,多而无彩了。”
宋辞把玉坠递给卿渺渺,“君子不夺人所爱,况且是美人所爱,姑娘,容我借花献佛,这个玉坠就送给你了。”
“这个,我与公子素不相识,我怎样好意思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。”卿渺渺推托。
宋辞轻笑,“举口就来的礼物,怎样算得上贵重呢,我一个大男儿,又无心悦的姑娘,我拿这个玉坠有什么用,姑娘若不嫌弃,就收下吧。”
卿渺渺接下玉坠,巧笑嫣然,“那我就先替公子收着这玉坠吧, 往后无机会,再还给你。”
“萍水相逢,若再相遇,那便是有缘了。”宋辞双手背负,挺了挺身姿,“姑娘,后会有期。”
卿渺渺望着宋辞的背影,嘴角溢着笑意。
如心用手肘撞一下卿渺渺,“小姐,你忘了夫人怎样教诲你的了,京城重地,切莫随意收别人的礼物,会给大人添麻烦的,况且,这是系身的东西,你怎样能收一个男子送的呢,那你是系在身上,还是放在屋里?”
卿渺渺把玉坠握在手心,“如心,你瞎说,这个分明是花灯上的东西,怎样就成了男子之物,再说了,这位公子一看就是商人,大邺有规定,仕穿锦商穿缎,商人是不允许穿锦绸的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如心还想说什么,好像也不晓得该说什么。
2.
卿渺渺再见宋辞,大概是两个月之后,那日城外的夫子寺周年庆,夫子寺向来香火鼎盛,听闻是有求必应,心诚则灵,卿夫人每年都要去那里添香油钱的。
卿南是大邺两朝丞相,总能逢凶化吉,除了他懂进退,审时度势,卿夫人觉得,少不了神佛庇佑。
卿渺渺陪卿夫人天没亮就来寺里,想着上头炷香的,只是她们还是来晚了,寺庙外面排了长长的队伍。
卿夫人叹息,“现在的人,越来越虔诚了,想去年我们来得还晚一些,还能赶得上头炷香的。”
卿渺渺扶着卿夫人安慰,“娘,我佛慈悲,佛祖不会介意你早一步晚一步烧香的,等会我们多添点香油钱就行了。”
卿夫人婉笑,“你呀,就是懒,早些叫你起来,还不情愿,以后嫁人随夫了,有些事情,还是你做妇人该做的。”
卿渺渺撒娇地说,“我还小,嫁什么人。”
卿夫人捏着卿渺渺的鼻子,“你呀,像你这么年岁,你姐已经嫁人了,还小,瞧你姐跟姐夫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,你若是有你姐一半温婉,也许早就许配人家了。”
“娘,我才不想那么早嫁人呢。”卿渺渺把头依偎在卿夫人的怀里撒娇。
如心轻扯一下卿渺渺的衣袖,指着寺里面,与静慧师太一起聊天的宋辞,“小姐,你看那位公子,是不是上次,上次花灯会撞见的那位?”
卿渺渺往宋辞那里望过去,灵机一动,“娘,你先等着,没准这头炷香有下落了。”
“哎,渺渺,别胡来……”卿夫人话还没说完,卿渺渺已经往寺门口走过去了。
守门口的尼姑双手合十,“阿弥陀佛,施主,寺里现在还没到时辰开门上香。”
卿渺渺双手合十,“师父,我是跟那位公子一起的。”
宋辞向卿渺渺走过来,“姑娘,我们又见面了,真是有缘。”
卿渺渺用目光示意,“你与静慧师太很熟悉?”
宋辞摇头,“今日第一次见面,不过,听闻夫子寺有求必应,我初来京城,想在这里求个平安,刚与师太商量,给寺里添一新庙堂,师太念我虔诚,便让我今天上头炷香。”
“添一处新庙堂,那得多少钱?”卿渺渺惊讶的看着宋辞,“我怎样看你也不像财大气粗的人。”
宋辞手握成拳放在嘴边轻笑,“姑娘,我是财大,并不气粗,以后可不要随便用财大气粗来称赞别人了,再者,钱财乃身外之物,能换个心安,已然是最好的用途了。”
卿渺渺不由打量起宋辞,他视钱财的态度,像极了父亲对权势的深思,父亲与先皇是忘年之交,父亲年少时,对先皇有过命的交情,先皇让他坐政扶持,年纪悄悄就给了相位,父亲不断躬身自省。
当初想与父亲结亲的达官人,把相府的门槛都踩平了,可父亲娶了商户出身的母亲,相敬如宾,就是有人想给父亲塞妾,都让父亲母亲婉拒了。
后来,先皇临终托孤,把皇上托付给父亲,父亲在野中说一句话,都要深思熟虑才说的,父亲说,他的一句话,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仕途,甚至影响到朝局。
父亲让两个兄长从小习武,保家卫国,却极少让他们参与朝政纷争,父亲说,朝堂上的事,没有绝对的对与错,卿家能替天下百姓做事就行了,不非得争得什么人前显贵。
父亲的意思是,将来他百年后,有脸面去见先皇,就足了。
宋辞轻唤一句,“姑娘,这么盯着一个男子看,似乎有些失礼。”
卿渺渺尴尬地低下头,咧嘴笑着,“公子,这头炷香,你一个人上不免浪费了些,介不介意,让我娘上一炷香?”
宋辞坦言,“无碍,让你娘进来吧,等吉时一到,你们就上头炷香,我与师太还有些事要商量。”
宋辞跟小尼姑说了几句话,卿渺渺招手,拉着卿夫人进去了。
卿夫人望着宋辞的背影,有些疑惑,“渺渺,那位公子是谁,我怎样觉得有些熟悉,好像在哪见过了?”
卿渺渺摸着后脑勺傻笑,“娘,我忘了问他姓什么了,娘,他是刚进京的商人,你肯定没见过他,这样吧,你们先进去上香,我去找他,总得跟他说声谢谢的。”
卿夫人凝目,“渺渺,那公子看着气宇不凡,你别毛毛躁躁的。”
“晓得了,娘。”卿渺渺扬着笑意。
后来卿渺渺已经想过,如果这次她听娘的话,没有毛毛躁躁,没有追上宋辞,是不是,她会跟姐姐一般,嫁得良人,一生两相依?
3.
卿渺渺在一个佛堂外面候着,大约等了一盏茶的功夫,宋辞便从里面出来,迎着半亮未明的朝阳,宋辞向卿渺渺走过来,他像一束温柔的光,轻软又温馨。
卿渺渺折着树叶,“你不是有事跟师太商量吗,怎样这么快就出来了?”
宋辞看着卿渺渺半会,把目光挪开,不至于失礼,“姑娘不是在等我吗,让美人久等,可是罪过了。”
“是不是,每个商人都像你这么油腔滑调的?”卿渺渺转身,没看宋辞。
宋辞往前两步,与卿渺渺并排而立,单手靠背,“能说会道,大概是商人的通性吧,不过,我说的句句失实,并非故添糖话。”
“你说你刚来京城,是打算在京城落脚吗?”
“嗯,春风酒楼就是我开的。”宋辞言语大方,跟他的人一样明朗,“在下宋辞,姑娘以后想找我,去春风酒楼便好,不过我不常在酒楼,在外面奔走的时间比较多,毕竟无妻儿,无牵挂。”
前阵子,京城的确新开了间春风酒楼,卿渺渺是晓得的,那酒楼开张当日,免了一日的流水席,此做派的确像宋辞这般,财大气粗的行为。
想到财大气财,卿渺渺不经意笑了下,她侧身,轻轻福身,“今日宋掌柜让香一事,渺渺略表谢意,改日必登门答谢。”
“区区小事,何足言谢。”宋辞用手轻抬,示意卿渺渺礼重了,他喃喃道,“渺渺,可是‘飘渺薄云舞,悠悠女鬼现’的渺渺?”
卿渺渺婉笑,她本想说她是相府千金的,但转念一想,会不会吓着宋辞,便把到口的话咽了回去,“正是此渺,生来渺小,不奢大志。”
宋辞敛了眉目,眼底有些温软,“生来渺小,不奢大志,有意思的名儿,渺渺姑娘,你知不晓得,有时候,平凡才是最难得的奢求。”
卿渺渺对上宋辞的目光,两人眼角含了些笑意,吉时已至,寺里开门放香客进来,一时涌进来的香客过多,几个孩子打闹追逐着过来,一个小男孩撞一把卿渺渺。
“小心。”宋辞眼快手疾,揽着卿渺渺的腰身,把她拉近怀里,避开小孩,冲撞间,两人的唇瓣碰在一起,摩擦而过。
卿渺渺双手抵在两人之间,宋辞的气味从她脸庞游过,她困顿地推开宋辞,后退两步,“宋掌柜,谢谢你,我,我先回去了。”
宋辞对着卿渺渺的背影说,“渺渺,听说,来夫子寺求姻缘的,一求一应,等会别忘了求上一支姻缘签。”
卿渺渺回过头,宋辞冲他笑了笑,“还有,记住,我叫宋辞,下次见面,别再叫我宋掌柜了,听着像叫个老头子一般。”
卿渺渺扑哧笑一下,小步走开。
4.
从夫子寺回来,卿渺渺整日开始有些茶饭不思,她拿着上次灯会上宋辞送给她的玉坠,细细观看,时而傻笑。
上次她真的去求了一支姻缘签,上上签:拔开云雾见花笑,不辞春风遇良人。
莫不是,宋辞就是她的良人?
“小姐,你一个人傻乐什么?”如心替卿渺渺换了热茶,瞟着她手里的玉坠,“小姐,想那位公子了?”
“别瞎说,让娘听到该误会了。”卿渺渺把玉坠系在腰带上,“如心,你觉得宋辞怎样样?”
“那位宋公子吗?”如心凝思了一下,“小姐见过的人无数,小姐说好便是最好的。”
“我什么时候说他好了。”
如心指着卿渺渺的脸比划着,“小姐脸上就写着,宋公子最好了。”
“如心,你笑话我。”卿渺渺嗔斥,却是春心荡漾,宋辞无论从谈吐,还是容貌,品行上,都占了极好的优势,哪个姑娘会不喜欢?
卿渺渺画了个好看的淡妆,柳眉如梢,两腮染红,她特意换了一身水蓝长裙,第一次与宋辞相识,她穿的就是这身衣裳。
卿渺渺独自去了春风酒楼,她环顾四周,却没看到宋辞,她有些失望,要了两盘小菜,在一旁坐了下去。
卿渺渺也不知本人坐了多久,依旧没见到宋辞,有些蔫气,她放下一锭银子,便离开了。
在春风酒楼旁边有处投壶,卿渺渺百无聊赖地在那里看了许久,心痒痒的,她给了银子换十根羽毛箭,她投了九根,一个也没中,平时她投壶技术还是可以的,也许是心不在焉吧。
卿渺渺把手中最初一根羽毛箭垂直正想放下,被一只大手握着,抬了起来,她倏然扭过头,心中惊喜,“宋……宋辞。”
宋辞温笑,“这么叫就对了,怎没到最初就放弃了,往往惊喜是留到最初的,不如我替你投一根,失礼了。”
宋辞说着,紧握着卿渺渺的手,另一只手揽过她的纤腰,头贴着她的头,“别看我,看前面。”
卿渺渺脸刹时涨得通红,把目光投到前面,宋辞一放手,果然投中最远的那个壶,老伯把壶里面的那支银钗拿出来,递给宋辞,“公子好手法。”
宋辞得意地应着,“美人在怀,手法能不好吗?”
卿渺渺退后几步,宋辞往卿渺渺靠近,替她把银钗子插好,“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,好歹是我们一起投中的,挺有留念价值的,渺渺,你说呢?”
“啊?”卿渺渺嘴角轻轻挪一下,不失礼数地笑了一下,“你怎样每次都神出鬼没的。”
宋辞没有应话,而是逼近卿渺渺,附在她耳边轻呓着,“渺渺,你今日与往日不同,你今日很漂亮,听说,你在春风酒楼等了许久,是特意等我的吗?”
卿渺渺脸轻轻发热,她性子虽有些大咧,却也是个闺阁姑娘,哪里经得起宋辞这么轻佻言语玩弄,“你少贫嘴,我之前说过要登门答谢,我从不食言。”
“这么说,你是承认,专承来等我的了。”宋辞侧目,肆意地盯着卿渺渺,“女为己悦者容?”
卿渺渺反驳,“是女为悦己者容。”
卿渺渺的目光撞上宋辞温灼的目光,他狡黠地露着一丝笑意,她一下子就意识到,被宋辞套路了,她躲开目光,盯着本人的脚踝,憋红着脸。
宋辞越过卿渺渺身侧,“来都来了,陪我吃顿饭,就当是你答谢我了。”
卿渺渺随宋辞进了春风酒楼,进了厢房,这里的小二的确是尊称宋辞为掌柜。
酒过三巡,宋辞捏着酒杯,透过浑浊的酒色,望着卿渺渺,目光温软,“渺渺,不知你可许配人家了?”
卿渺渺夹菜的手搁了一下,她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,把筷子放下,“宋辞,你这话问得,似乎有些唐突了。”
“是有点,但我必须晓得,你有没有许配人家,才好拿捏着分寸。”
“什么分寸?”
宋辞仰头,把酒一饮而尽,他慢慢地放下酒杯,随着杯子落下,嘴里飘出一句话,“你若许配人家,我与你该保持距离,我该把对你的喜欢藏在心底,你若没许配人家,我便可以大大方方地坦露心声。”
卿渺渺没料到宋辞说得这般直白,她端着的身子有些虚,宋辞敛了眉目,温言,“渺渺,你没回答,我就当你没有许配人家了。”
卿渺渺紧张地扣着桌面,“宋辞,你吃醉了。”
宋辞走到卿渺渺旁边,拉起她的手,卿渺渺手心明显渗着汗,有些冰凉,“渺渺,我清醒得很,不管你信不信,那日花灯会,我对你便有些情愫,后来在夫子寺遇到你,我更确定,我喜欢你,你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,我们都生来渺小,不奢大志,如今你就是我的大志了。”
卿渺渺紧垂着视线,“宋辞,我们算下来,只见过三次面,你说这样的话,是不是急了些。”
“缘份的事,没有急缓的,你若是觉得我诚意不够,我明日就去府上提亲,对了,你府上是哪里?”
卿渺渺焦急地抬头,“别,先别去,我想等我们相处一段时间,觉得合适了,再让你去见我爹娘。”
宋辞激动地说,“这么说,你是同意与我共赴一生了?”
卿渺渺没有点头,也没有摇头,半晌才说,“谁说与你共赴一生了,没准后来我发现不喜欢你了。”
宋辞把卿渺渺拥入怀里,“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卿渺渺没想到,幸福来得这么突然,她感觉还有些迷糊,不太真实。
5.
卿渺渺与宋辞背着父母私下往来了两个月,她对宋辞的感情,越来越笃信。
那日父亲刚从朝堂下来,卿渺渺把父亲与母亲叫到一块,神奥秘秘地说,“爹,娘,女儿有件事想跟你们说。”
“什么事,神奥秘秘的。”卿南看着卿渺渺,打趣地说,“该不会是相中哪个男子,想嫁人了吧?”
卿夫人瞅着卿渺渺娇羞的样子,紧张起来,她拉着卿渺渺,“不会是真的吧,上次夫子寺那位公子?”
卿渺渺悄悄点头,用余光瞟着卿南,卿南忖思片刻,“女大不中留,只需是你们两情相悦,爹不会过于插手你这事的。”
卿夫人也随之点头,“那位公子我瞧着,一表人才,是个温和的人,约个时间,让他来府里跟我们见见面再说。”
卿渺渺得到父母应允,咧嘴高兴地笑着,“娘,宋辞是春风酒楼的掌柜,他说了,要约你们去春风酒楼见面的。”
卿夫人赞许地说,“春风酒楼开得那么大,它的掌柜竟是个年纪悄悄的小伙子,这宋辞是吧,看着应该不错。”
卿南脸色凝重,“等一下,渺渺,你说他叫宋辞?”
“是呢,爹,有什么问题吗?”
卿南眼底浑浊,“当今皇上五王子安亲王就叫宋辞,渺渺,你别跟爹说,他们是同一个人?”
卿渺渺先是愣了一会,摇摇头,“不,怎样可能,爹,宋辞他,他就是一个商人,春风酒楼是他的,这个他骗不了我,他……”
“渺渺,别说了。”卿夫人突然扼着卿渺渺的手腕,“渺渺,他就是安亲王,娘一年前与安亲王见过一面,怪不得那天在夫子寺远远见着,我就觉得似曾相识,渺渺,这安亲王我们惹不起。”
卿渺渺惶恐地望着卿夫人,“娘,你告诉我,这不是真的。”
卿夫人安慰卿渺渺,“渺渺,京城多得是大好男儿,我们不嫁皇室。”
卿南叹息,“渺渺,如今东宫空悬,安亲王和楚怀王最无望稳坐东宫,楚怀王手握兵权,又有战功在身,而安亲王深得民心,爹不排除安亲王有意接近你,是为了东宫之位。”
卿渺渺倒吸口凉意,想起与宋辞相处的种种,从相识到相爱,都是一场不测,并且,宋辞并不晓得,她是相府嫡女,她执意摇头,“不,宋辞不会骗我的,我要去找他问清楚。”
卿渺渺起身,往外面跑出去,卿夫人焦急,“相公,你快去把她追回来,渺渺跟小小不同,渺渺一旦陷进去,就回不了头了。”
“这条路,总归要她本人走出来了,明日我去见见安亲王,此事,容后再说吧。”卿南深思着。
6.
卿渺渺去到安亲王府,见到宋辞,一切言语都显得惨白无力。
宋辞拉着卿渺渺的手,“渺渺,我没有骗你,春风酒楼的确是我开的,我开春风酒楼,只是行善,而我与你说的每一句话,都是真的,我没有跟你坦白身份,只是担心会吓着你。”
卿渺渺推开宋辞,冷漠地看着他,“那你又晓得我是什么身份吗?”
宋辞温言,“渺渺,我喜欢的是你的人,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,都不冲突的,我的王妃,只要你。”
“宋辞,我叫卿渺渺,我是卿南的女儿,来给我提亲的达官贵人,要把卿府的门槛都踩平了,京城是个藏不住事的地方,你会不晓得我?”卿渺渺眼底蒙上薄雾,“王爷,你是从一开始就想接近我的了吧,你晓得我卿家的姑娘不嫁仕郎,所以,你就隐瞒身份,与我虚情假意,对吧?”
宋辞无辜地摇头,“渺渺,我的确不晓得你是丞相的女儿,我们相爱在先,我对你是真心的。”
卿渺渺哽噎,她望着宋辞,一字一句地说,“宋辞,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,对不起,我们的事,就此作罢吧。”
卿渺渺一步步后退,倏然转身离开。
宋辞追着卿渺渺出了院子,他扼着卿渺渺的手腕,拉着她入怀,扳着她的后脑勺,灼热的吻侵战着这片薄唇。
卿渺渺用力争扎,她双手推着宋辞,宋辞的吻越渐狂热,她咬破宋辞的唇,宋辞并没有放开,舔着血腥与泪水的苦涩,他舌尖探进卿渺渺的唇齿间。
卿渺渺慢慢软服下来,双手徒然放下,又环上宋辞的腰间,两人吻了许久,都有些气背,宋辞才放开卿渺渺,他捧着她的脸,双目猩红,深情地说,“渺渺,山风不歇,海水不涸,我绝不负你,如果你觉得权势对你是一种压迫,我可以离京,我什么都不要,我只需你,没有你,我活着都没有意思了。”
卿渺渺嘴唇颤抖,“宋辞,你真的情愿为了我,放弃一切?”
“我命都可以给你,还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的?”
卿渺渺垂了泪目,“宋辞,山风既歇,海水若涸,我依旧不负你,我卿渺渺这辈子,只嫁你一个。”
宋辞扬起嘴角,眼角溢出一丝湿润,深深吻住卿渺渺的唇,两人紧紧拥抱,抱着未来不明的感情,他们是彼此心里的依靠。
至多,宋辞对卿渺渺来说,是真的,无可代替了。
7.
宋辞并没离京,那天卿南去见了宋辞,宋辞言之灼灼,他是爱卿渺渺的,如果卿南觉得,让他放弃东宫之争,才情愿把卿渺渺嫁给他,他完全情愿放下一切。
卿南说,大邺的君主,不该让他一个朝臣来妄论,他只需确信,宋辞会不会真心待卿渺渺。
后来,安亲王娶了相府千金,这事在京城激起一些暗涌,让那些在野局上站立不明的人,有了些蠢蠢欲动。
北蛮动乱,不用宋辞开口,朝廷过半官员赞同卿琅挂帅出征,楚怀王手上的兵权,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落在卿家。
卿琅凯旋,宋辞被立为太子,这多少是倚着卿家的功劳。
卿渺渺成亲的第三年,宋辞继位,那天封后大典上,宋辞拉着卿渺渺的手,受着群臣朝拜,宋辞当着大家的面说,“卿渺渺永远都是朕的皇后,一辈子都是。”
宋辞几乎做到了,后宫等同虚设,虽也选了几个大臣的女儿入宫,却独宠卿渺渺,夜夜厮缠,他与卿渺渺等同寻常人家过日子。
那晚一翻云雨后,卿渺渺躺在宋辞怀是,手指划过他有胸膛,略得失落,宋辞不解其意,把她圈在怀里,“皇后这是怎样了,一下子就没了兴致。”
卿渺渺微抬目,深思过后才说,“皇上,你以后也去别的宫里留宿吧,雨露均沾。”
宋辞捏着卿渺渺的鼻子,“皇后今天怎样说起这话了,莫不是不,皇后这么快就厌弃朕了,我们成亲才五年。”
卿渺渺摇头,把头埋进宋辞怀里,“皇上,臣妾是越来越爱你了,爱你当然要替你着想,臣妾与你成亲五年,未曾怀过孩子,你是大邺的天子,这事耽搁不得。”
宋辞翻身,把卿渺渺压在身下,满目灼热,“渺渺,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,你还年轻,整个太医院都在替你调理身子,太医说你身子微寒,是可以调理的,相信不久之后,我们会有本人的孩子的。”
“皇上……”卿渺渺目光泛红,她是多么不情愿把宋辞推向别的女人怀里,听到宋辞这么说,心里既感动,又内疚。
“这种话,以后不许再说了。”宋辞温软地笑了笑,吻住卿渺渺的唇,久久缠绵。
8.
宋辞的情话,不过躺在锦熹宫的榻上,说了两载,与卿渺渺缠绵两载。
边镜在卿家两子的守护下,久得昌平,而卿南作为三朝丞相,位高权重,臣民敬戴,卿家多少有些功高镇主。
宋辞让卿渺渺劝卿家父子,在野堂上言出无状,再做些损害百姓的表象出来。
卿渺渺甚是不解,宋辞讨好地说,“渺渺,这不过做些表象,骗骗天下百姓的,如今这天下,说是朕的,可天下的臣民,都盯着卿家,唯卿家是首,朕答应你,只是顺势要回兵权,并且,你爹早就说过,辞官归乡了,你爹做了一辈子的丞相,爱惜名声,你替朕去劝劝他。”
卿渺渺不可思议地望着宋辞,“皇上,你让我爹辞官归乡,我兄长归还兵权便可,何必还要演这出伤害百姓的戏?”
“渺渺,卿家的威望在百姓心中,已然树立起来,长此下去,朕这个皇上,天下人都说是卿家替朕打下的了。”
卿渺渺执意摇头,“皇上,我爹从来躬身自省,没越过一丝规矩,全心全意替大邺守着江山,我兄长用命替大邺守着和平,当初也是你把兵权放到他们手上的,如今闹这一出,着实寒了父兄的心。”
宋辞脸色沉凝,他没了平日里的温软,“卿渺渺,是不是,连你也觉得,朕的这个天下,是卿家打下来的,朕娶了你,才做了太子,稳坐皇位?”
卿渺渺愣了一下,“皇上,臣妾没有这个意思,臣妾只是……”
宋辞拂袖,“皇后,你是大邺的皇后,朕对你一心一意,就算你生不了孩子,朕也从无半句责怪之语,你要惜福,本人好好反省吧。”
“不是……”卿渺渺的话还没说完,宋辞就气恨恨地离开了,这是宋辞第一次跟卿渺渺说重话,卿渺渺觉得云里雾里的。
那天晚上,卿渺渺在回廊上坐了一宿,宋辞第一次没来锦熹宫过夜,卿渺渺回想以前的种种。
出嫁前夕,父亲叮嘱她,伴君如伴虎,安亲王极可能是大邺未来的天子,你要戒骄戒躁,凡事思而后行。
母亲说,渺渺,我看你爹这大半辈子在官场上打拼,每日忧心忡忡的,往后你要过的,便是你爹这日子,娘是千万个不情愿,既然你喜欢,娘也不阻止你,难得的是,安亲王待你极好,只是,你记住一点,你的行为举止,代表着整个卿家,一人犯错,全家共罪。
卿渺渺不敢想象,若是卿南真的做了什么出格的事,罪行摆在跟前,宋辞会真的如他所说的,只是免其官职吗,卿南一辈子的好名声,怎能说毁就毁。
几日之后,宋辞才再来锦熹宫,依旧是旧事从提,卿渺渺态度坚决,“皇上,恕臣妾无能,如果皇上觉得卿家功高镇主,臣妾自请离宫。”
宋辞盯着卿渺渺看了许久,从嘴皮里挤出一句话,“卿渺渺,你也想陷朕于不义是不是,朕分明当着朝臣的面说过,你这辈子都是朕的皇后,你想让朕废后吗?”
卿渺渺目光坚定,“皇上,既不能废后,是不是,臣妾死了,就可以免了卿家的罪过,这一切,不过是因臣妾而起。”
卿渺渺拿捏着茶杯,恍恍失笑,“皇上,卿家的一切,都是你给的,你要拿回去,一句话的事,今日是兵权,明日是卿家的命,是不是,下一个,就该轮到臣妾这个一无用途的妇人身上了,是,你是说过,卿渺渺这辈子都是你的皇后,你不会废后的,也对,活着是皇后,死了不就得啊么?”
宋辞恼怒地瞪着卿渺渺,“卿渺渺,你狂悖。”
卿渺渺隔着泪目,“卿家生我育我,我护着他们,怎样就狂悖了?”
宋辞夺过卿渺渺的茶杯,丢摔在地,满殿宫女跪了一地,宋辞冷笑,“皇后行为乖张,即刻起罢去六宫主权,禁于锦熹宫,无诏不得出。”
卿渺渺倔强地望着宋辞,两人四目相对,直至宋辞愤然离去,她豆点大的泪水才顺着眼角,滑落下来。
卿渺渺不晓得,到底是本人的狂悖惹恼了宋辞,还是宋辞被她窥空心思,恼羞成怒。
9.
中秋过后,那夜月明高空,锦熹宫突然走水,待宋辞走来到锦熹宫时,熊熊的大火,触目惊心。
宋辞激动地想要冲进火海里,被宫人拦了下来,宋辞身边跪着几个妃子,还有太监宫女,“皇上,保重龙体啊,你切不能进去,皇上,你要替大邺的百姓想想啊。”
宋辞跪倒在地,盯着那场大火,双目赤红。
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时辰,卿渺渺被抬出来时,面目全非,太医跪在宋辞面前,“皇上,娘娘是先自刎,才引起这场大火的,娘娘身上有浓重的油味,娘娘是死心已决,引火自焚的,皇上,要节哀啊。”
宋辞抱着卿渺渺的尸体,他身体瑟瑟发抖,嚎啕大哭,“渺渺,你怎样就这么傻,我们还有大好的日子,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你的命,我只是想好好做个君主,我怎样就错了。”
“渺渺,你用不着用你本人来保全卿家,我说过的,我真的不会伤害卿家的,那是你的至亲,你怎样就不相信我了。”
“渺渺,你回来,你说过要陪着我一辈子的,渺渺,渺渺……”
宋辞的哭声在这片废墟中回荡着,撕心裂肺。
宋辞与卿渺渺相爱的时候,卿渺渺就说过,等哪天宋辞变心了,她就把本人烧成一撮灰烬,不给他留下一寸尸骨。
原来,深爱时的戏话,等不爱了,就成了真话,那晚,宋辞抱着卿渺渺的尸体,在那堆废墟中,坐了一夜。
番外.夙离
1.
我叫夙离,从小看着母亲在洇河上卖唱,母亲嗓子好,皮相好,每日专程来听母亲唱曲的人,只多不少。
从小耳濡目染的,我也长了一副好歌喉,母亲甚至说,我唱得比她唱得还要婉转动听,但是,母亲从不让我开嗓,母亲说,我这一开嗓,这辈子就步了她的后尘,没有活路了。
是的,母亲一点活路也没有了,靠着卖唱,把本人嫁给父亲,过了几天安生的日子,父亲经商失败,染上赌博,母亲用嗓子换来的钱,都不够填父亲的赌债的。
父亲对母亲拳打脚踢,嘴里还骂着污晦的言语,说母亲赚的钱,不干不净,说我是野种,母亲是克星。
在债主又一次上门讨债,父亲企图把母亲卖给债主时,母亲趁夜带着我逃了出来,绝望之际,母亲抱着我跳了洇河。
母亲没了, 我却活了下来,我被一位公子救了下来,六岁的我,有了重生,有了救命恩人。
救我的人竟是当今的五王子,我睁开眼看到的第一眼,宋辞那张温善的脸映入视线,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,“醒了,她醒了,母妃,他醒了。”
“醒了就醒了,大惊小怪的。”妇人不耐烦地应着。
透过月色,我依稀看到宋辞腰间的玉佩,红得跟血一般。
后来,我再醒来,便是在宫里了,宋辞央着丽妃把我留在他身边伴读。
宋辞不过比我年长四岁,他个子却比我高出半截身子,我总是要抬头才能看到他。
宋辞说,“夙离,在宫里,你只许抬头看我,你不许这么看着别人。”
我脸上憋急,我以为这是宋辞对我的偏爱,却不知,在宫里这么抬头看奴才,是大不敬之罪。
2.
宋辞十八岁封王出宫,丽妃替宋辞挑了几个合心眼的丫头过去安亲王府,我是宋辞唯逐个个,自动要带出宫里的。
我不断觉得,宋辞对我,是区别对待的,宋辞也调侃过我,说我与他青梅竹马,按戏本上唱的,我是要与他结亲,我羞煞着脸,或许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我整颗心,都悬在宋辞身上,我晓得,我配不上他,只需远远看着他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后来,安亲王府进来了两个男子,时常伴在宋辞身边,他们说话的时候,宋辞不准任何人靠近,那日我经过书房,隐约听到两个男子与宋辞谈话。
“卿家二小姐,是个灵活的姑娘,相爷说过,卿家的姑娘,不嫁仕郎,要想娶这位二小姐,一定要诚心,并且,先讨二小姐的欢心,出其不备,让相爷无反驳之力。”
“你去帮我把这位卿小姐的喜好,还有行迹,都给我查得仔细心细的,区区一个官家小姐,我还不信我讨不了她的欢心了。”
这是我听过宋辞说过最笃信的话,这句话像针尖咯在我心口一般疼痛。
3.
宋辞变了,变得不爱跟我说话,变得整日与那两个男子细究,怎样讨好卿家二小姐。
我第一次见卿渺渺,是她冲撞着来王府,责怪宋辞欺骗了她,卿渺渺绝望地说,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,我想,这是一个多么明理的姑娘。
可是,卿渺渺终归是爱宋辞的,爱得义无反顾,我亲眼目睹他们在院子里亲热,如果不是听到宋辞之前与男子说的那些话,我一定想深信,宋辞是爱惨了卿渺渺。
一个王爷情愿放下身段,放下权势,与你双宿又栖,卿渺渺怎样会不掉进宋辞的温柔乡里呢?
宋辞成亲前夕,他突然把我找来,他盯着我看了许久,突然说,“夙离,我需要你。”
我惶恐地望着宋辞,“王爷,奴婢愚笨,不知你这话什么意思?”
宋辞轻抿着嘴,“夙离,卿渺渺嫁进王府,我想让你在她身边服侍她,不用太刻意在她身边走动,只需要帮我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”
我倏地下跪,宋辞这是想让我与他同流合污,是的,同流合污,“王爷,奴婢笨手笨脚的,怕做不好。”
宋辞走过来,握着我的手把我拉起来,“夙离,你在我心里,从来都是与旁人不同的,夙离,我需要你,除了你,我不晓得找谁帮我了,你帮帮我,行不行?”
“我……”
宋辞把我拥入怀里,“夙离,等事成之后,我们就可以明正言顺地在一起了。”
我羞怯,却坚定地点头了,我生来最忌做恶人,却贪恋这本不该有的温暖。
4.
我在卿渺渺的院子里做着最不起眼的事情,掌灯,卿渺渺几乎从来没留意到我的存在,我整日看着她与宋辞和和美美,好不愉快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但是,我每日都会做一件事,就是在卿渺渺的汤里面散上一种红色的粉沫,宋辞并不隐瞒我,那是一种让妇人无法怀子的药,宋辞说,他不能让卿家拿捏着,卿渺渺不能生下她的孩子,就算要生,也不能生下王府的嫡子。
后来,我随卿渺渺入宫,我从那个不见天明的地方出来,又回到那个,见不得光的地方。
在卿渺渺入宫的第三个月,她有喜了,太医没告诉卿渺渺有喜的消息,而是去告诉宋辞了。
宋辞找的我,我才晓得,卿渺渺有喜了,我第一时间,竟是替卿渺渺高兴。
宋辞盯着我看,目光严厉,“夙离,是不是你做的?”
我张着口,半晌,硬是没说出半句谎话,然后点头,下跪,“皇上,娘娘好不容易才得来这个孩子,这也是你的孩子,你就让娘娘生下来吧。”
宋辞扶起我,眼底隐晦,“夙离,你傻啊,渺渺这身子,现在就算她怀有孩子,也保不住的,只会伤了身体。”
“皇上,你帮帮娘娘。”我带着哭腔说。
宋辞背过身去,“夙离,以后没经过我同意,不准冲动行事了,这事别让渺渺晓得,朕会让太医偷偷把孩子流掉的。”
我咬着嘴唇,舔到丝丝血腥,“皇上,你爱娘娘吗?”
宋辞大概没料到我有此一问,他凝思半会,回过头来,对着我的目光,坚定地说,“当然爱,我爱渺渺,才更爱惜她的身体,我不能让这个孩子要了她的命。”
瞧,说得多冠冕堂皇,情深意切的,就是这么一个人,夜夜与卿渺渺欢爱,日日让我在卿渺渺的汤里下药,却说着这世间最动听的情话,整个后宫都说,皇上爱惨了皇后娘娘。
我看着平静的宋辞,心里发怵。
后来我不止一次想跟卿渺渺坦白,但我说不出口,我不知从何开口。
5.
宋辞软禁卿渺渺,这事情于我来说,不算惊讶,意料之中,只是来得比我想像中的要快一些。
锦熹宫的宫人,一夜走光了,只要如心跟我依旧守着锦熹宫,宋辞说过,我什么时候想回到他身边,随时都可以。
我却慑了,选择留在锦熹宫。
我终于看着卿渺渺从一个灵活的丫头,一步一步地变成深宫怨妇。
卿渺渺问我,“夙离,大家都走了,你为什么要留下来。”
我跪在卿渺渺跟前,“娘娘,奴婢是来服侍奴才的,奴才去哪,奴婢就去哪。”
卿渺渺看着我,突然红了眼眶,“哪有像你这么傻的人,从一而终的。”
我想,卿渺渺大概想说,她才是她嘴里那个傻人吧。
后来,宋辞有大半年没锦熹宫,卿渺渺会跟我说起从前往事,说起她那个嫁给商户的姐姐,说起卿家的家教,说起从前与宋辞的恩爱。
我偶有提起,我是被宋辞在洇河上救起来的,我的阿娘葬身在洇河那里。
卿渺渺徒然望着我,“夙离,你是不是喜欢皇上?”
我倏地跪下,“奴婢不敢。”
卿渺渺隔着泪目,却笑了,“藏在心底的爱,比拥有虚情假意的好多了,真想重新走出这宫殿,看看外面的风光,没有宋辞,没有伤害,没有爱。”
6.
中秋过后,卿渺渺越发地少话,有时候一呆,就是一整天,卿渺渺似乎动了轻生的念头,卿渺渺说,这一切都是她引起的,如果没有这桩亲事,卿家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,她死了,卿家也不会被宋辞忌惮了。
后来,我寻了如心,拿了卿渺渺那个整日握在手心里的玉坠,让她去寻宋辞,说娘娘有悔改之意。
我记得,那天晚上,星空明朗,好像那夜,我在洇河上,睁着微薄的目光,第一眼看到宋辞时的月色一般,软软的温暖,我情愿相信,宋辞的心,已经洁白无瑕的。
我递给卿渺渺一杯茶,“娘娘,喝口茶润润喉。”
卿渺渺木然地接过茶喝了下去,我婉婉发笑,“娘娘,如果有一天,你无机会从宫里走出去,记得,每逢三月初八,替奴婢去洇河放上一个冥船,我怕我娘再也找不到她的船了。”
卿渺渺惊愕地瞪着双目,她抓着我双手,一个劲地摇头,“夙离,你想做什么,你这话什么意思,你不能做傻事。”
我推开卿渺渺,“娘娘,奴婢从来就不是个好人,对不起,你原谅奴婢吧。”
卿渺渺晕了过去,我事先寻了两个侍卫假扮成倒粪桶的宫人,把娘娘扶进桶里,推了出去,并给了他们一块令牌,那块令牌是进宫后,宋辞就给我的,他晓得我每年三月初八,都要出宫去洇河一趟。
我想,宋辞心里,大抵也给我留了一席之地,不管是不是爱。
其实受过卿家恩惠的人很多,想找一些人协助卿渺渺出宫,比我想像的简单。
我换上卿渺渺的衣裳,往身上倒了油,点了火把,用匕首抹了脖子,一切顺顺当当的,我想,等宋辞赶到的时候,我一定被烧得血肉模糊了。
卿渺渺,宋辞欠你的,我替他来还给你的,你们两清了,宋辞,我与你,恩也好,怨也罢,我们也两清了。
我生来最忌做恶人,我曾也想做个普度众生的好人,可惜我胆怯,贪生,我修行不够,豁不出本人的命,舍己救人。
我到底是做尽坏事,这个时候竟然不忌死色了,如果,那年,我没有遇上宋辞,没有多活这十几年,会不会好些?
尾声:
大邺皇后葬身火海,皇上悲痛不矣,大赦天下,卿家父兄三子,辞官返乡。
三月初八,洇河旁边有个穿着白衣,戴着斗笠的女子,手里拿了一张冥船,却又折身回了车上。
如心扶着女子的手,“小姐,为何不去了,这几年,你都去放冥船。”
女子望着不远处站着的宋辞,“有人替她放了,走吧,回去。”
女子闭目,没有再望一眼宋辞。
那么警惕的宋辞,后来寻不到夙离,大概也猜到,那日在锦熹宫葬身火海的,并不是卿渺渺,是他亲手救上来的夙离。
只是,那晚,夙离死了,卿渺渺死了,宋辞也死了,活着的,只是卿家的二姑娘,还有,大邺的天子。
(完)
往期精彩放糖:
作者:白梦,头条首发原创。
原创不易,欢迎原处转发分享,禁复制二转。
下一篇:返回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