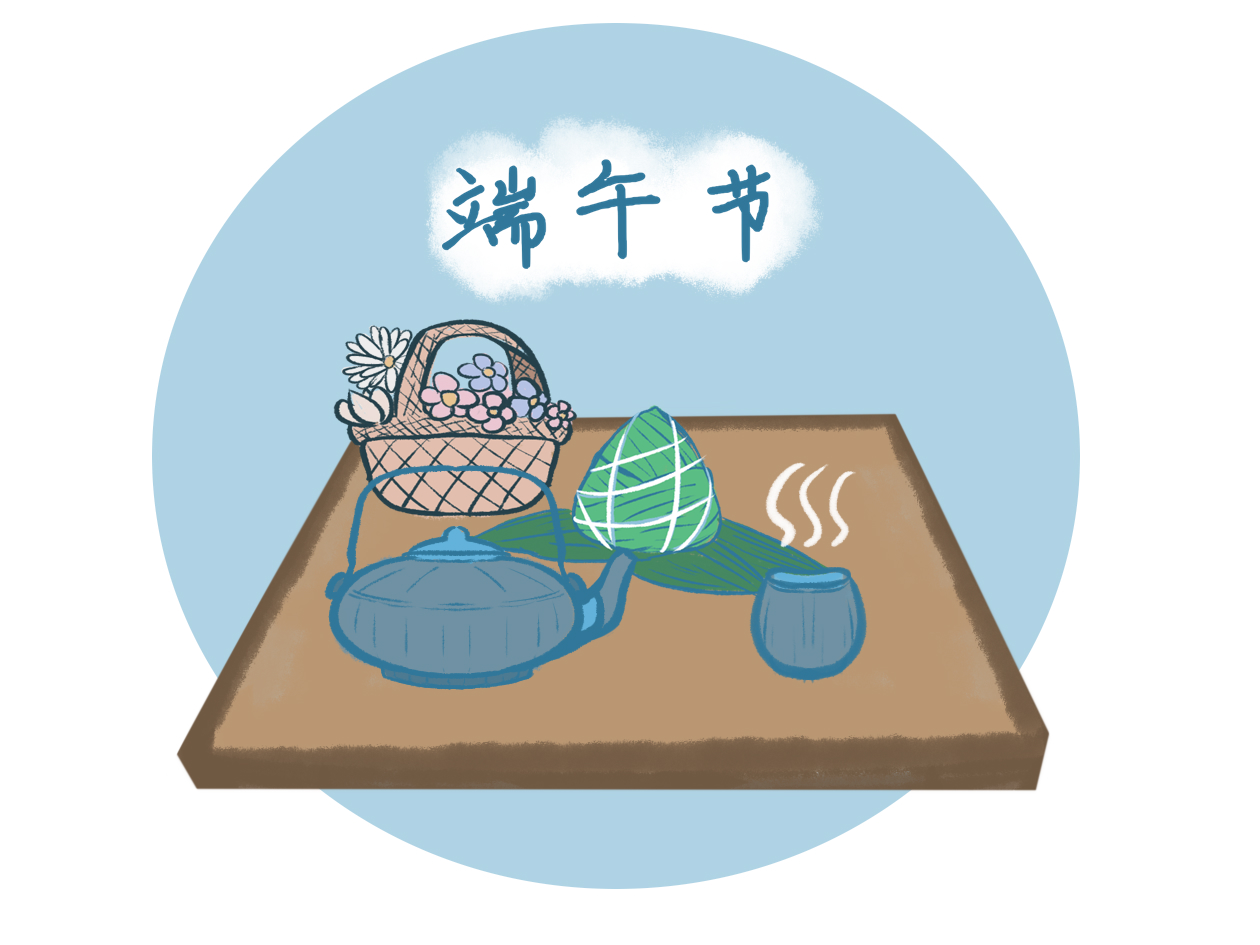老家荒山上一颗不晓得活了多少年的橡子树有一个矮矮的小土堆,不晓得的还以为那只是一堆土,其实那是我发小人生的归宿…… 又是一个寒冬腊月天,我早早地背上收拾完行囊回到了老家。老家是偏僻的山区,偌大的村庄只要二三十个人在家务农,正是腊月份,村里的人都在山上割龙须草,都指望着卖了龙须草买年肉过年。我一个人闲来无事,就在山上四处溜达,看看这生我养我二三十年的小山村,感觉一切都还是老样子,但又跟以前不一样,有一种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的感觉。 半夜吃完饭,天下起了毛毛雨,邻家小爷也在家待着,于是就到他家串门,一阵寒暄过后,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他家屋檐下闲唠嗑。不晓得怎样地,突然就扯到了生老病死这一块了,正在跟小爷扯现在医疗条件好,人都长寿呢。 “啥都长寿,你那个小学同学洋鬼子可到年轻,去年不也死了,人的命谁说得准?谁敢说谁一定能活到几岁。”小爷漫不经心地对我说。 “啥?谁死了?”“我们上边村那个刘洋,就是那个你们小时候天天一起玩的那个娃儿,你不天天问人家叫洋鬼子吗,这回可真正成鬼啦” “真的假的?啥时候的事?他咋没的?我咋不晓得?”我一脸难以相信的表情。“哎嘛,我都七八十的人了,我骗你娃子这干啥,再说了,谁没事拿这种事开玩笑,这种事敢乱说吗?”小爷面带不悦地说道。 “咋回事?小爷你好好说说呗,我都不晓得咋回事?”“你当然不晓得啦,你一年到头就过年回来那么几天,大过年的谁来给你说这种事,那不是诚心妨你嘛,他也不晓得是得啥病?好像是白血病吧。” “那就是得病也不可能说没就没了啊,那玩意咋说不也得过一段时间才不行吗?” “他得病都两三年了,村里面低保都有他,球!你成年不在家,你不晓得,前几天他妈还在我们后山干活呢”一时间我竟然有点难以接受,不晓得说啥好了…… “他不还有个弟嘛?”“幸亏他还有个弟,不然他爹妈不哭死才怪呢,这人呢,一死啥都没了,他妈上回还说他死了大家都好,他也不遭罪了,我们也不用往那个无底坑里砸钱了,就慢慢挣钱还钱就行了” “他妈咋这样呢?那好歹也是他亲儿子啊!”对于他妈的话,我感到气愤,同时也感到些许的悲凉。“你娃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,那是不想给他治?那是治不好!都是泥巴腿子能挣多少钱,你说我这一天割龙须草,从早割到晚,一天才挣几十块钱,他家为他都砸了几十万了,现在都欠一屁股的账呢,这还咋治,去医院医生都跟他爹妈说,让他回家保守医治,没多大的希望,你娃子还不行着呢,当爹妈的哪能狠心看着自家娃活活死在本人面前?”说着小爷掏出烟点了一根,猛吸一口长长地吐了出来。 闻着那呛鼻子的烟味,感觉眼睛也难受得要紧。 “那他的后事咋整的?”“啥咋整的!一切从简呗,他没成家,不能进他家的祖坟,只能买个白茬棺材给他装了,埋在那边荒山下面的橡子树下面。” “不对啊,那地方没有坟呢,我上次还路过那呢,都没有花圈啥的,哪有坟?”“你懂个球!那刘洋都没有后,按我们这的风俗,只能给他用白茬棺材装了,然后给他埋了,还不能用砖给他垒墙,只能用几个石头给他堆一下,这里面说法多着呢。” 霎时脑子里脑补出了一副场景,内心不由得疼了一下…… “那地方咋上去啊?路不好走,棺材咋抬上去?”“哎呀,我说你那学咋上哩,用挖掘机呗,用几根粗绳绑着棺材,挖掘机的爪子吊着上去,到地儿了,挖掘机再刨两下,一个坑不就成了!” “那找几个人帮忙抬上去不行吗?好歹送他最初一程吧,这样整多草率啊”我问道。“不跟你个糊涂蛋儿说了,跟你娃子说不清,不断跟你说,他没有后,谁给他戴孝,你去找人抬,那是得上门给人家跪着磕头求人家帮忙的,你说他一个晚辈,他又没有后人,叫谁去求人呢” “哎……”我长叹一口气,也不晓得说什么好……脑海里霎时想到了我们两个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情景,那时候多开心啊,无忧无虑的,一起上学,放假了一起溜达着呢,下河捉鱼,上山找野鸡蛋,十来年同处时光的点点滴滴都涌上心头,心里五味陈杂。随后又跟小爷天南海北的胡扯一番后,就回家做饭去了,然后一整夜辗转反侧,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……第二天清晨,天还下着毛毛雨,我独自去那颗橡子树下看看了,那里哪有一个坟的样子,雨水早已把土堆给冲得不剩多少了,只要几个大石头还在,这似乎是唯逐个个可以证明这里已经有一个坟的证据了吧。 四周一片荒凉,怎样也想不到这里竟然有一个已经爱说笑的男孩儿在此长眠。站在他的坟前,看着仅有的几块石头,想想人生有时候其实也挺可悲的。“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”,若我百年之后,几十年过后,能否有人能记得何处是我的坟头呢?就像我的发小一样,待到这棵橡子树倒了以后,谁又能晓得他究竟埋骨何处呢? 我们都是这世间的过客,何必在乎能否会留下传说,岁月静好,一切且行且珍惜吧!
下一篇:返回列表